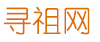八楼刘之名林------官家林
官家林,是依汶镇隋家店八楼刘家族的私家林墓,因葬下多位“官员”而得名,在八楼刘家谱中称之为“龙王坪”茔。
该地坐落在依汶镇隋家店村西3里,是一块小冲积平原处,面积不大,有三四亩地,南依汶水,北靠峻岭,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质地绵软,汶河和峻岭如同两条巨龙在这里相聚,大有龙脉之气象,故称此地为龙王坪,是一块名符其实的风水宝地。该地原属隋家店村,现属小保护村。
该官家林的使用方位为座南朝北,也就是南依汶河,北对峻岭,即纳汶河之灵气,又采崇山之精华,是一块“龙”地,风水自然独一无二,无与伦比。道光年间,正在兴盛时期的隋家店八楼刘,需要新置林地,请了最高水准的风水先生进行选地,最后选中了这块叫做“龙王坪”地块。但是,这块宝地的风水好是好,但是这是一块“回龙地”,它南依汶河,北靠峻岭,与传统的坐北朝南、依山傍水的风水观念极不相符。为了占用这块风水宝地,他们就采取了倒行穴的办法,其墓葬方向,一律坐南朝北,背水对山,这在讲究风水的年代是绝少有的,是一个相当特殊的选择。据老人家讲,这种选墓地方法,一般人家是不敢问津的,只有相当有势力的家庭才敢一用,当时,隋家店八楼刘正在兴盛之时,家有2000亩地,门前竖着八个旗杆,停着八个官轿,文官到处下轿,武将到此下马,在京里做着主事老爷。这样的家族,选这样的林地,也是很正常的事。
后来这块“回龙地”先后葬了历城县训导刘遵辂,道光丙午举人、候补知县刘汝先,浙江候补典吏刘汝历,候选训导刘汝功等多位官家人,有了这么多的官员下葬在这里,因此,后来的人们也就称这块林地叫“官家林”。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块林地地处非常偏僻,且隐藏在树林之中,很少被人们发现,也很少被人们所关注,因此躲过了无数的劫难。现在,这座官家林里的坟墓基本保持完好,碑碣基本保持完好。只是碑碣上那一行行优美的文字,经百余年的风剥雨蚀,显得有些摸糊。
八楼刘之名林------主事林
史海钩沉之二
主事林,因安葬主事老爷刘遵和而得名,坐落在依汶镇隋家店村东,界(湖)至蒙(阴)公路南侧。现被四周民居民包围,成为典型的村中“林墓”,但在八楼刘家谱中被称之为“圭峰山前茔”。
据当地老人们讲,主事林绝对是上上等的好风水,她北依圭峰山,南对汶河水,山脉和水脉在这里交汇聚拢,绝对是出大官的气象。后来实事也证明这一点。
第一个葬进主事林是刘文翔,也就是主事老爷刘遵和的父亲,他是八楼刘第八楼主刘琈的重孙,是从上高湖过继到隋家店来承祧刘檀一支的。这个刘文翔是太学生,沂水道光版县志称之为重孝友,讲敦睦,为族乡党所推重。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是,刘文翔教子有方,所生五子,皆科举及第,贵显朝野,被称之为八楼刘“文五虎”。其中,长子刘遵和,考中进士,官至户部主事,从三品,在京为官三十年。次子刘遵夔,官至巨野县教谕;第三子刘遵辂,官至历城县训导;第四子刘遵侨,官至东阿县教谕;第五子刘遵侃,先任莱阳府学训导,后升为江西南昌府经历。这样一来,刘氏兄弟五人个个为官,人人入仕,门庭显赫,成就了后人难以超越的辉煌。刘文翔因子而贵,因子而显,被诰封为奉直大夫,晋政大夫,朝议大夫,户部主事加三级。
这“五虎兄弟”的下一辈也很出色:刘遵和的儿子刘汝循是太学生,刘遵侨的大儿子刘汝先是道光丙午举人,候补知县;二儿子刘汝历是浙江候补典吏;三儿子刘功汝是候选训导;刘遵侃的大儿子刘汝赢是补典史。刘遵和去世后,随父葬于圭峰山前茔。刘遵侨去世后也葬于圭峰山前茔,刘遵和之子刘汝循,刘遵夔之子刘汝棠去世也都葬于圭峰山前茔。因此地葬的最大官是主事老爷,这个林也就被称为“主事林”了。史海钩沉之三 八楼刘之名林------知府林
知府林,坐落在蒙阴县垛庄镇石汪河村李家沟自然村,因葬有大明府知府刘翰明而得名。这里地处孟良崮(芦山)西麓,巍巍孟良崮就从这里隆起,这里是孟良崮的起点的源头,是绝佳的水风宝地。
据八楼刘道光谱载:大明府知府刘翰明葬于北庄东北石井茔。石井,地名也,现在北庄东北石汪河村李家沟自然村东岭和东小峪村南岭交汇处的深壑之内,因四周皆为峭壁,中有细泉涌出,终年不竭,清澈甘美,形同石井,故得此名。石井北侧,散落着几个大坟墓,从形制上看,当年应是实力不小,但不是大明府知府刘翰明葬处。
据知情人介绍,葬刘翰明的知府林,在石井东北1公里处,其方位是座东北向西南,也就是东北高西南低,土质为黄粘土。它北靠凤凰山,南依石井溪,依水傍水,风水自然甚好。凤凰山是孟良崮(芦山)西麓第一个垄起的山脉,石井溪是孟良崮(芦山)第一滴溪水发源地,占两个第一,可见风水之妙。
关于刘翰明的生平,康熙十一年沂水县志专门载文给予褒扬:刘翰明,大名府知府,博学笃行,后进多籍其引掖。居恒赈人之急。庚辰、辛巳大饥,道殣相望。公赈穷乏,赖以全活者甚众。及登仕,三任皆称廉能,善政未易殚悉,大约平反冤狱以数百计,殆所谓“有于公隐德”者。其刘氏家谱载:博学笃行,明崇祯拔贡,清初任陕西华阴县知县,升直隶真定府同知,大名府知府,署大顺广兵备道事,授中宪大夫,政绩载县乘。
刘翰明的墓被扒的时间是一九四七年。传说,刘翰明下葬时是金头银胳膊,扒墓人就是冲着金头银胳膊来的,但是扒来一看,没有什么金银,只扒了一些朱砂。刘翰明祖的墓很大,很高,是砂灰预制的,墓碑很气派,后来被人砸了,再后来残碑就不知去向,只剩下一块残缺的护林碑,标着知府林的四至和方位。
这些年来,为了沾一点知府林的风水,附近的居民都争着把自己的先人葬到这里,如今知府林的上方,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头,可是令人遗憾的,这些坟主的后人也没出一个像样的官儿。
2012清明时节,刘翰明裔孙数百人,踊跃而来,重新为刘翰明筑坟立碑,并在墓前叩首长跪,焚纸献供,声声礼炮,惊天动地,响彻云霄。史海钩沉之四 八楼刘之名林------旗杆林
旗杆林,坐落在蒙阴县垛庄镇八刘数发祥地——北庄村西北二公里处,其方位是杨树底村黄河巷子沟自然村村后,因此处有一个官封大旗杆而得名。这个大旗杆的主人就是八楼刘三世祖刘士科。
刘氏家谱中记载,刘士科的葬处是北庄西北茔。这个茔地为何叫作旗杆林呢?说起来话有些长,刘士科有个孙子叫刘翰明,名崇祯拔贡,官至大明府知府,应了那句祖以孙贵的古语,刘士科养育出大明府知府刘翰明有功,被皇家追赠为中宪大夫,大明府知府。这刘士科有官衔在身,他的墓前就竖了大旗杆。从此之后,这里的大旗杆就成了刘士科墓地的标志和名片。久而久之,后来人们就把北庄西北茔的刘士科墓地叫作旗杆林了。
旗杆林是一块绝佳的水风宝地,她坐落在孟良崮(芦山)西麓沙岭凹处,坐北朝南,三面环岭,成太师椅状,有聚水敛风之功,又有藏龙卧虎之势。从任何方位来看旗杆林,你只能看到一片丛林,其他的什么看不到,这叫作藏而不露。据当地老人讲,这旗杆林正北枕着一块巨石,巨石的名字叫月亮石,正南踩一座小山,山的名字叫踏帽盔山,旗杆林因此就有了“头顶月亮石,脚踏帽盔山”的传说。这帽盔山,松青柏翠,形如官帽;这月亮石形制巨大,中有银色月牙,熠熠生辉。上有月亮照着,下有官帽托着,有这等好的脉气和风水,这刘氏后人如何不发达?
关于这片林地的选择,成书于道光年间的《刘氏家谱》作过专门记载。作者是已卯进士、户部主事刘遵和。他这样写道:刘氏起家寒素,自沂后世耕读越数传,族姓日盛,非祖德曷臻此,闻北庄西北茔之获兆也,有羁客留数月,濒行指地相赠,是固客思图报,抑吾祖数世积累,默默中假此日者指授,为吾刘氏蕃昌之始基也。这个正式家谱中的文字记载,与旗杆林的传说是相符的,说是有一个南方旅客,路过北庄时,贫病交加,倒在荒山野坡之中,素有善心的刘士科得知后,立即将旅客接至家中,供以饭食,施以医药,待若上宾。数月之后,旅客康复,临别时刻,将自己勘察好的这块风水宝地,指赠给恩人刘士科。这样个记载和传说,不管是真是假,旗杆林的风水有没有发挥作用,这已是历史悬案,难以作出更准确的厘清,但是有一个不争的实事是,从刘士科这一辈开始,这一支后人开始兴盛起来。刘士科的三个孙子刘不竭,刘弼明,刘翰明皆出类拔萃,其中,他的三孙刘翰明崇祯拔贡,官至大明府知府,他的八个曾孙刘庆、刘瓆、刘璨、刘玕、刘瑗、刘瑸、刘璩、刘琈更是个个优秀,人人入仕,以八座楼分家立户,成就了令人称颂的八楼刘的辉煌,后来的八楼刘就是这里开启的发展大剧。
由于历史原因,旗杆林多年失修,破坏严重,所有石碑无一兴存,只剩下了一块残缺的旗杆座石和半截防林碑。2012年清明,刘士科的后人相聚到旗杆林,为刘士科筑坟立碑,用最隆重的大礼,祭典这位具有标志意义的先祖。八楼刘之名门——光裕堂、德裕堂
光裕堂和德裕堂,是八楼刘众多堂号中的佼佼者,原址在沂南县岸堤镇岸堤村中心,现为岸堤社区文化广场。这里前依大汶河,后靠高湖河,两河相汇,如同双龙聚首,形成了独特的风水,成为富甲一方的宝地。岸堤镇乃历史名镇也,文化深厚,源远流长,是沂蒙山区腹地政治、文化、经济的一个中心,这里逢一排六大集,设有汶河码头,是洋货进山和土货东去的集散地,历代的沂水官府都在这里设置管辖机构,国民政府曾在这里设立九区,共产党的山东抗日军政学校就设在岸堤的南庙。
八楼刘是何时何人到岸堤开创基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八楼刘分家说起,大约在清康熙年间,家住垛庄北埠庄的刘庆、刘瓆、刘璨、刘玕、刘瑗、刘瑸、刘璩、刘琈叔兄弟八人,需要分家立户,每人分得了一座楼,这就是八楼刘的来历。老八刘琈,在分家时分得了上高湖楼,人也就从北庄搬到了上高湖。刘琈的父亲刘翰明曾任大明府知府,刘琈官至宁阳县教谕,候补行人司司副,生有六子,四子刘广涵被分到岸堤安家创业。刘广涵生有四子,二子刘植生有三子,二子刘炳礼,生有一子致恭,致恭生有两子,长子汝庆,次子汝喜。汝庆生有两子,长子家承,次子家登,这兄弟俩人分家时,把大宅一分为二,一家一个堂号,家承为光裕堂,家登为德裕堂,每个堂号有田地120顷,这就是光裕堂、德裕堂的来历。
光裕堂和德裕堂门相连,户相挨,一墙隔两家,其具体的位置是:光裕堂在东,德裕堂在西,都坐北朝南,都有前大街和后大街,位置十分优越。光裕堂占地十多亩,为二进院落,大门口临街朝南,进大门口有东西耳房,内住看门人,迎面有房屋3间,廊柱结构,西耳房与迎面堂房处有一月亮门,走月亮门可进入后院,后院有正堂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全为廊柱结构。院东为马棚,大门街南为柴草园,后有便门通北大街。解放后,此宅为供销社物资存放处,院东的马棚改建为供销社饭店,柴草园改建为五金门市部、百货门市部,后供销社搬迁,原建筑拆除,建为民宅及村委大院。
德裕堂占地也在十亩上,大门口朝东南,进门为一院落,南边为一溜耳房,耳房中开便门,东西厢房各三间,堂房为过厅三间,全为廊柱结构,沿西厢房北侧西入西跨院。西跨院有堂房三间、西房三间。从东院过厅或西院堂房东山与东院过厅西山之间可进后院。后院也有堂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此为内宅。经内宅往后有一座砖石垒砌的三层楼房。楼有便门通后大街。耳房便门、过厅、后院、楼房在一条中轴线上。该楼房虽面积不大,但是整个岸堤的制高点,易守难攻,在兵荒马乱时,人们常到楼上避难。抗日战争时期,此楼被日本鬼子炸毁。解放后,此宅为岸堤区政府所在地,后区政府搬迁至西岭,原建筑拆除,后辟为民宅。
光裕堂后期的主人是刘曰华,育有五子,长子刘同厚,二子刘志厚。1938年8月共产党的队伍来到岸堤后,即参加了革命工作。1948年9月,山东党政军各级组织抽掉大批干部去东北开辟工作,刘志厚随军驻进东北,后在东北病故。三子刘江厚、四子刘思厚都在临沂上过中学,曾回乡教书,以后去了台湾,最后定居日本。五子刘权厚建国后曾在供销社工作,后到东北定居。
德裕堂后期的主人是刘曰练,育有三子:长子刘来厚,后去东北定居;二子刘因厚,后去垛庄小峪子定居,曾任村支书;三子刘敬厚,后去马牧池定居。另刘曰练有一侄刘章厚,抗战时参加革命工作,建国后在济南工作。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05年冬天,我因公到岸堤出发,热心发掘传统文化的岸堤镇第二中学的语文教师、校刊《岸柳》的主编张祥生老师,不辞辛苦,陪我去考察光裕堂、德裕堂旧址,使我拍下这两个堂号大门残存的资料照片。我和张老师的这一举止,还引起了一位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和讥讽。随后,张老师又在百忙中走访了大量的知情人,写出了珍贵的光裕堂、德裕堂的原始资料,并附了简图,还原了当年光裕堂、德裕堂的辉煌历史,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他这种热心爱传统文化,一丝不苟的做法,令我十分感激。可惜的是,两年之后,热爱传统文化的张祥生老师,不幸英年早逝,我们失去一个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去年夏天,因续修家谱需要,我专程去岸堤搜集有关光裕堂、德裕堂的资料,发现这两个远近闻名的古堂号旧址已不复存在,残石断砖也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建的社区文化广场。
我徘徊在这块故土上,想寻找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什么东西也没找到,我是知道什么东西也不会找到。作为一个爱好捡拾传统文化碎片的乞丐,我只是职业病的又一次发作,做出这种毫无用处的寻找。
别了,光裕堂;别了,德裕堂!兴旺庄刘家林大墓主人考证
坐落在岸堤镇兴旺庄村花岭北麓的刘家林,有一个高大的墓茔,因年代久远和墓碑破坏,这座墓茔的主人已佚去名讳,成为多年来困扰后人的一大疑惑,亟需找出正确的答案,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知情人的减少,这个悬案将会永远被历史所尘封。
本人自七八岁开始,便随父文厚先君,到这个林上给先祖们添坟上坟,并且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么大的一个林,就只有我们一家来上坟。当年,我虽然能从父亲嘴里知道一些关于这个大林的史料,但是因我少不更事,加之社会环境特殊,对老人说的陈年旧事当作耳旁风,很少往心里拾,这就造成了这个大林史料的断层和缺失。
父亲对上坟之事非常重视,每到东南寒节,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寒风凛冽,甚至是是贫病交加,他总是虔诚的备好纸香供品,到大林里祭祖上坟,每次还下令我必须去。有时候,家里穷得连买盐的钱也没有,父亲就腆着老脸出去借两角钱,买几张纸到林里烧一烧。有一次,为了上坟的事,我的母亲发了火,她说:你除了婧受了这几十个土堆子,还有一个压死人的富农成份,你还有什么?说得父亲哑口无言。还有一次,我们的一个邻居对我父亲说:这个林的后人不光你自己,就你们自己上坟,你把钱花到那几个破坟子上,有谁值你的情,憨巴了是不是吧?还不如把省下来的钱,买盒子烟抽。
母亲说的是对的,我们家婧受的坟墓是全村最多的,共有两个林,一个叫作北林,另一个叫南林。北林就是前面说花岭北麓的祖林,南林就是我们这支自己新建的林,因处在花岭南而得名。我统计了一下,北林有二十二个坟子,南林有九个坟子,这个数字的确是不少,上坟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别人家都是三两个坟子,到林里上坟,三下五除就搞定了,而我们家则不行,得用上大半天的工夫,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 别人家上坟往回走了,而我们家的一个林还没压完坟头纸,由此可见,我们为上坟的付出有多大。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最怕父亲叫我去跟他上坟,但是不去是不行的。我随父亲上坟的主要任务是压坟头纸,就是给每个坟头压上一张新的烧纸,这个压坟头纸的任务也不是好玩的,需要满林里跑,需要每个坟都要爬上去。给北林的那个最大的坟墓压坟头纸最是困难,当时,我觉得这个坟子就象一座大山,又高又陡,身小力薄的我,直接爬是爬不上去的,得退出好几十米,助跑一大阵才能攀上去,再很费力地找一块石头压好烧纸。父亲很执拗的要求,压坟头纸土块是不行的,见雨就化开了,有风就吹了,必须是用石头才行,但是合适的石头不是很多,要获得一块好的石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每年上七月十五坟,常常是下雨天,地里粘的拔不出脚来,走几步就得抠一下泥,浑身都是泥水,把人整个半死,十分难受。最要命的是,坟堆上长着很多乱杂树,叶子上藏着成串的八甲子,一旦碰上,又痛又痒,十分难受,每次上坟我都会被扒个五七六下。在上过年坟时,冰天雪地,冻得人伸不出手来,压个坟头纸就更难了,根本找不到可用的石头,就是找到了,也是被冻着,无法取下来,只能用手指抠,用脚踢,手指抠出了血,脚也被踢肿了,真是苦不堪言。
北林大墓上有一怪事,就是墓基上有两个坟头,这件怪事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为什么一个坟子两个坟头呢?我问了好多人,大家都说不知道,后来,我仔细观察,发现这个大墓根本不是什么两个坟头,而是由于坟头太高了,当年平坟的人,为了省事和省力,就把大坟头的泥土往两边扒,这样虽然把主坟头扒没了,却在两边堆起了两个小坟头,这也就造就了一个大墓两个坟头的奇观。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坟头曾被村里的青年突击队双平了一下,种了不少高梁,长得还不错。后来,我步量了一下,这个大墓的直径七米多,坟高五六米。村里的老人们说,这个大墓是全村最高的林,坟前还有最大的石碑和最高档的香炉。后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大劫,墓碑已不知去向,香炉也不知去向,大坟也被蚕食的越来越小,失去原有的辉煌。如今,这座大墓四周已露出沙灰。
关于这个墓的主人名讳,家父曾对我作过交待和说明,那时我无心无脑,没有听进去,失去了这个铭家族文化的机会,及至年长,我对家族文化有了新的了解,对家族的事有了热情,可是,父亲已经不在了,这让人后悔不及,父亲去世后,我所能做的,就是接过了给这两处大林上坟的任务。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曾对我说,人不能忘了祖宗,人不能没有根,我们是这些坟墓的后人,如果我们不来上坟,这些坟就成了无主坟了,无主坟就会让人平的,如果祖林让人当无主坟平了,我们这些后人是没脸活了。可以这样说,兴旺庄刘家大林只所以在历次运动中能保存下来,最关键的一条是,这个大林还有人护着,还有人去上坟。有一次,村里的一个官找我父亲做工作,说:这么大的林就你自己上坟,你也怪累的,以后就别去上了,咱当无主坟平了吧。一向软弱的父亲,说了句硬话:你先把你们家的祖林平了,再平我们的祖林。父亲还告诉我,这个林还有很多后人,他们很早以前就搬走了,以前的时候,盘山庄、南沿麓、葛墟的本家都来上坟,现在只有南沿麓的本家还来上坟了。我曾问过父亲,别人家为什么都搬走,为何只留下我们这一家,单家独户的,受人欺负,父亲说,你还小啊,大了你就知道了。
关于这块大墓前的石碑去向,我曾花费了很多工夫和精力去寻找,我曾找过当年参加破旧四旧的老干部,他们回忆说,可能是当了桥板,也可能是当作柴油机底座了,我找遍了村里所有小桥,却无一收获。最靠谱的说法是,在建高级社的时候,村里进了一台大柴油机,得找一个大石头固定下来,选来选去,最后选了这块大石碑,后来,这大柴油机晃得很厉害,就把这块石碑晃碎了。这块石碑也就失去了踪影。就这样,这个大墓主人的名讳也就无可考证了。
2009年的一天,一个偶然机会,我得到了近支本家爷爷刘曰才的联系地址,他是南下干部,在马鞍山钢铁厂做过官,我曾满怀希望给老人连去了三封信,附了图表,询问老家大林的情况,可惜的是,我这位爷爷当时已87岁,他回信说自己年纪大了,记忆也不清楚了,他回的信说是我们的祖林在杨树底,我们和葛墟的、南沿麓的是一家,其他就不知道了。他的这个说法,让我产生了更多的迷惑,这个杨树底是个什么地方,在何处?后来我查阅家谱资料,才知他说的杨树底,是三世祖刘士科祖葬的地方,地址是蒙阴县垛庄镇杨树底村的旗杆林,他说我们的祖林在杨树底是对的,只是有点远了。这也难怪,我这位爷爷是一个南下干部,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就没回来过,也从来没写过信问一问爹娘的坟墓如何添土上坟,他对我们父子两代人几十年如一日,为他的父母添土上坟的事,从没提一个字。我小时候,曾对这件事有一些小情绪,给他们家的坟上压坟头纸的时候,就多少有些轻慢。后来,我年纪稍长之后,对此事就想开了:他不给他的父亲上坟,那是他的事,我们给他们家上添土上坟,是我们自愿的,没有什么困果关系。
我和这位老爷爷取得正常联系后,我曾计划去马鞍山去看一趟这位前辈,就家族的一些事当面向老人请教,遗憾的是,还未成行,这位爷爷就去世了。我的这位爷爷有三个儿子,对我来讲,是三个叔叔,年纪也在六七十岁了,他们也对家族的事不感兴趣,我们 琈祖后续谱工程启动后,组委会给他们家打过数次电话,他们一个都不接,给他们发过三次挂号信,他们一封也不回,他们这种态度,这在全家族中是少有的。但是,他们并未和老家真正失去联系,他们还和老娘门上有来有往,只是不联系本家人罢了。但是,本着对他们这一支后人负责的态度,编委会还是把刘曰才老爷及三位叔叔的名讳在家谱上填写清楚,并注明了外迁去处,以备他们的后人认祖归宗。令人欣喜的,通过这次续修家谱,我们终于搞清楚了兴旺庄刘氏这一支的脉络:这一支是琈祖第四子广涵的后代,广涵置业岸堤,育有三子,第三子刘炳文,太学生身份,迁居兴旺庄,兴旺庄北大林的那个最高坟墓是他的,立林时间推定为康乾朝时代。用今天的眼光看来,他这个墓地选得也是很有水平的,该墓座南朝北,背靠花岭,前望汶水,土层深厚,风水独好。特别一时的是,此处为汉文化遗址,秦砖汉瓦残随处可见,历史文化蕴藏十分丰富。刘炳文有七子,长子遵经,其后人不知去向;二子遵纬,其后人留守兴旺庄;三子遵恒,其后人迁沂水;四子遵织,其后人迁金佛院、盘山庄五子遵盟,其后人不知下落;六子遵宪,其后人迁南沿麓。七子遵传,其后人正在查找中。
需要补充的是,炳文的第二子遵纬育有两子,长子汝福、次汝佑,这兄弟俩另立林新林,选址花岭东坡,这就是兴旺庄刘家的南林来历。汝福葬于花岭坡南林,其子家晋迁往葛墟,从此这一支在葛墟定居。汝佑有两子,长子家安,次子家荣,南下干部刘曰才的爷爷就是家安,本人的老老爷爷就是家荣。这样一路数来,炳礼支在兴旺庄守望的就只有家荣这一脉了。